楼下老周一口蒜泥白肉下肚,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嘴上辣得打颤,筷子却根本停不下来。
我赶紧递过去一杯冰镇啤酒,笑着说:“老配方,老火候,吃的不是肉,是记忆。”
这道菜在我们家传了三代,从我二舅那学来的。早些年他在成都跑馆子,天天跟后厨师傅腻在一块。说起这道蒜泥白肉,得从长江边的搬运工讲起。
那年月,挑水的、扛麻袋的,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,汗珠子掉地上都能砸出坑来。吃饭要快,还得扛饿。于是聪明的川菜师傅就想出这么一招——把五花肉煮得软糯,切得薄如蝉翼,再来一泼热油激着蒜香,一口下去,立马觉得腰不酸腿不疼。
别小看这几片肉,工夫可一点儿不省。做这菜,跟相亲一样,全靠“第一印象”。肉选得不好、蒜打得不细、油泼得不准,全都白搭。
现在说话容易,一顿饭点外卖就行。可那会儿,吃口肉得攒半月饭票。现在想想,哪是吃菜,那是吃着岁月磨出来的滋味。
肉怎么煮得嫩?老辈人有说法,叫“三进三出”。不是让你跑澡堂子,是说煮肉的时候得讲火候:冷水下锅,水一沸立马捞出,凉了再来。这过程得反复三次,目的就一个,让肉更紧实,口感更细腻。
我头回试,水还没烧开锅就溜去看球赛,回来一锅肉跟泡面一样软趴趴,儿子夹一筷子直摇头:“爸,这肉像喝醉了。”
还有个讲究,肉煮完不能直接切。得晾,得挂,得吹透。通风处吊个钩子,肉挂上边,下面接盆冰水。我头两次晾得不够透,切的时候肥肉跟瘦肉闹分家,夹起一片就跟拼图一样散架。闺女一边吃一边笑,说我这是“白肉拼图盛宴”。
到了捣蒜这步,那就更讲究了。家里石臼都快被我磨平了。蒜瓣拍扁、撒盐、画圈搅。这不是做菜,这是磨性子。有一回我贪方便用料理机,结果蒜泥打得跟水似的,还苦得直冲脑门。媳妇嘬一口,眉头立马拧成了麻花:“这是蒜汁儿不是蒜泥!”
泼辣椒油这步,堪称全剧高潮。油温太低,香味激不出来;温度高了,一锅全糊。烧油得听“动静”:一响炸辣椒、二响爆芝麻、三响定颜色。我烧了三锅,屋子里弥漫着“焦香味”,才摸清门道。
切肉这事也不能心急。肉得切在它微热的时候,太热会散,太冷就硬。我那刀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,刀背上还有旧主人的刻字——“快刀斩凉肉”。每次切完三片,我就得磨一下刀,那感觉就像给老伙计加点油。
最后一步——摆盘,看起来简单,其实最难。我一次试图玩点花样,把肉片摆成宝塔型,结果刚淋上红油,整座“塔”瞬间坍塌,丈人笑我“建筑结构不过关”。后来我学乖了,黄瓜卷底、肉片盖上去,圈着浇红油,每片肉都穿着红衣裳,艳得像舞台上的川剧小生。
这些讲究说多了你以为我是矫情,其实不过是对吃的那点尊重。有人说,做饭是浪费时间,我偏不信。厨房里哪有浪费,全是生活的回音。
说个真实事。上礼拜,我弟来家串门,学着我做蒜泥白肉,非要搞创新——往红油里加了巧克力粉,说这样能增加“甜辣平衡感”。我一听差点没把菜刀扔了。他还煞有介事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,起名叫“摩卡风白肉”。结果点赞数居然翻倍,我气得直翻白眼,结果评论区全是:“哇,好有创意!”“下次试试!”
那晚我坐在窗前看天,天边晚霞红得像被泼了辣油。厨房飘出的蒜香还没散,我脑海里却全是那句老话——“自家的锅台,炖得下五味杂陈”。
楼上的王婶隔着窗户喊:“你那红油还剩吗?拿我那坛腌萝卜换!”我一边应着,一边想着,食材可以换,手艺不能丢。
你说,这年头哪还有谁愿意花两个小时捣蒜?哪还有几个孩子知道石臼是什么?可不做这点细活儿,生活就像一锅没下盐的汤,看着满满一锅,其实寡淡得很。
厨房的事儿,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。有时就是那么一勺油、一片肉、一缕蒜香,把一家人从四面八方唤到桌前。你夹一口,我喝一口,饭桌上少了仪式感,可多了点人情味。
这不,昨天我刚收拾完厨房,阳台那边飘来香味,我知道,是楼下小张学我泼油了。他家新装的厨房灯把窗子照得亮堂堂,我站在窗前看着那盏灯,心里竟也暖暖的。
现在想想,那肉片上的红油不仅是味道,更像一层温柔的旧时光。吃完一盘蒜泥白肉,不光是嘴上留香,心里也踏实了不少。
窗外的风吹进来,轻轻拂过碗边的红油星子,我没擦,留着——就当是生活留下的指纹吧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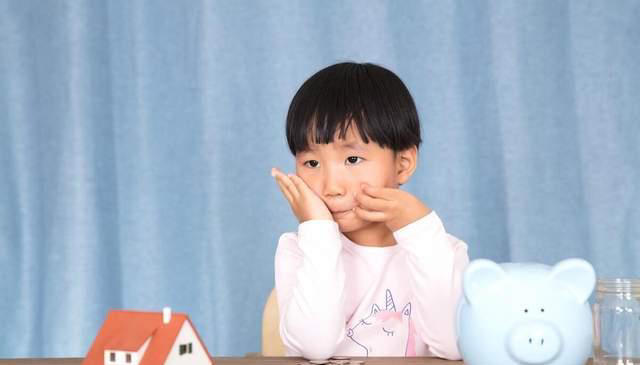






0 留言